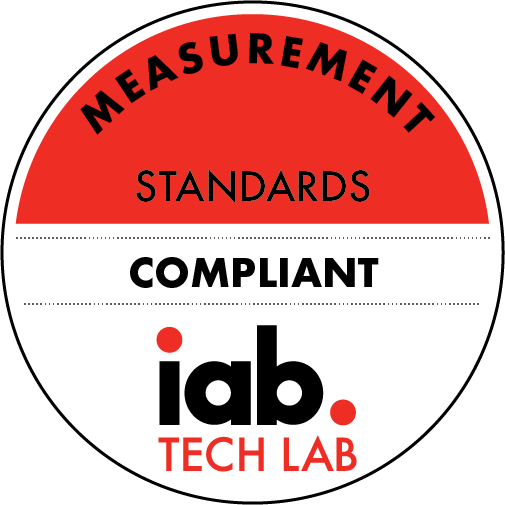Episodes
Published 04/22/20
Published 04/22/20
赵淑敏/文 也许天生命苦;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,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,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,不吃绝不感遗憾;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,我也能随缘“表现”欣赏,不惹人厌,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。 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,说:“留着,馋了的时候,就抓几个来吃。”“我从来不馋什么!给我,万一放坏了,糟蹋了不好。”不要扫兴,你会想吃的。”可不,扫兴多煞风景,我不该扫人兴。收下了那些吃食,且尽责地吃光了。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,到底没肯丢掉,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。 人问,什么最好吃?答曰: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。 ...
Published 04/22/20
Published 04/22/20
Published 04/20/20
Published 04/20/20
喻丽清/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,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。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。可惜年轻时,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? 最近收到北医大“北极星诗社”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《望远文报》,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,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。谁知它依然健在,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。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,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,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。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,草稿不知如何打起,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,我们未必心服。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,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,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。回顾所来处,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,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。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,使我们着迷于哲学,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,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,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。我记得萧孟能的《文星》和林衡哲的“新潮文库”,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。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,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,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。...
Published 04/20/20
Published 04/17/20
陈若曦/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,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,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。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,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,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,于下午三点开始,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,陪伴孩子做功课、读报,或带动游戏、唱歌,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;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。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,有隔代教养的,也有孤儿,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。 今年夏初,有志工建议: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,到外地去参观游览,开开眼界多好! 好主意。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,于是开始筹募经费。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。她给会里发出信息,会员纷纷响应,一人一千,很快募到四万元,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。志工们的费用,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,等用完再说。...
Published 04/17/20
Published 04/15/20
Published 04/15/20
宇文正/文 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,后来看相声瓦舍“战国厕”的段子,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,他们已经借“影剧六村”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,我笑说:“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!”儿子追问:“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?”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,我很不情愿地承认:还真的有,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,忘了几岁开始,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,才不再去公厕。但记忆里,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,那个公厕一直还在,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,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,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。 那天我玩耍经过,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,一边跟我讲话,不知怎么,哐啷一声,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,破了。我惊恐地望着她,隔好久才说出话来:“怎么办?你会不会被你妈骂?”她的表情倒是镇静,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。这时她母亲(是蔡妈妈?刘妈妈?……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……)从厕所里走出来,微笑地对我说:“为什么要骂?盘子总是会破的。”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,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,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。...
Published 04/15/20
Published 04/13/20
孟东篱/文 盐寮,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,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。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,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,月眉山不高,只有一两百公尺,经多年砍伐,已没有多少树木,但杂草遍山,倒也葱绿,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,碧蓝辽阔。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,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、芬芳沁人的野百合,据我所知,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,大把大把采去,渐渐的,野百合终于少了。 今年,雨停之后,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,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,有的躺在地上,有的浸在水盆里,有的插在瓶中。不上学的时候,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,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,走在路上。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,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! 孩子们采野百合,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,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,一朵两块钱。也有人来收购,一朵两块,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。可是这些花,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!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。这些花,就是耶稣所说,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。 而今,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,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,都会被采光,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。...
Published 04/13/20
Published 04/10/20
Published 04/10/20
林黛嫚/文
台湾女作家,著有《闲爱孤雪》、《闲梦已远》、《闲人免爱》等。
《小林来台北》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,收录在《嫁妆一牛车》那本短篇小说集,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,还提到“小林来台北现象”,“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,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。”是啊,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,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,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?
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,都有不同的背景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,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,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。“来来来,来台大;去去去,去美国”,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,台大就在台北,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,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,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。
...
Published 04/10/20
Published 04/08/20
林清玄/文
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。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。看着朋友安详的脸,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,现在他终于解脱了,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,感到有一点安慰了。
走出殡仪馆,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,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,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告诉自己:“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!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。”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。
然后,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,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,我端起咖啡,对自己说:“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!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。”这样想,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。
喝完咖啡,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。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、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。
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、求姻缘、求子嗣的思主公庙,香火鼎盛,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。
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,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。
...
Published 04/08/20
Published 04/06/20
Published 04/06/20
袁琼琼/文
台湾女作家、编剧,著有《春水船》、《自己的天空》、《随意》等。
一直以来,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,我总说编剧,没法说自己是作家。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。或者说,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,如果说自己是作家,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。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。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。说自己是是编剧,人家会问,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,一本剧本要写多久?都是非常具体的。但是作家,如果有人问“写一本书多少钱?”“写一本书要多久?”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,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。
“作家”的好处是,那是“进行中”的行业,就算八百年没出书,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,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:“多久”和“多少”从来没有个定数,总觉得“不知道哪一天”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。因此,一日作家终身作家。有前总统,前总裁,前校长,前经理,但是从来没有“前”作家,只有死了的作家。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,一日作家终身作家。
...
Published 04/06/20
Published 04/03/20
杨逵/文
本名杨贵,台南新化人,著有《杨逵全集》十四卷。曾获东京《文学评论》第二奖(首奖从缺),是首位进入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。
台北近郊有阳明山,彰化近郊有八卦山,高雄近郊有寿山;都距市区很近,交通方便,眺望甚佳,是郊游散步的好地方。
我喜欢这些地方。也住过一段时间。
很早我就看中了台中近郊的大度山,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,种些花木水果,过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。
就是这个梦想,促使我借钱在东海大学前买了这一块不毛之地。
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不毛之地。
理由很简单:“有毛”之地太贵,买不起。
买了之后,饱受孩子们的反对与朋友的责骂,说我这个幻想家自讨苦吃。
孩子们各有所好,对此荒地没有信心,自然不能合作;又没有钱雇工帮忙,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,实在是注定有苦吃了。
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,我决心苦干下去。
吃苦我不在乎,在我一生中,苦是吃惯了的。
...
Published 04/03/20
Published 04/02/20